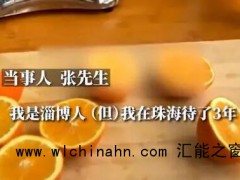国务院港澳办谈涉港议程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5月22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发表谈话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有关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该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依法防范、制止、惩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的宪制责任。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时,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通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和对香港原有法律制度的尊重。然而,香港回归近23年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被严重污名化、妖魔化,加上香港原有相关法律长期“休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权力配置方面存在诸多缺失,导致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实际处于世所罕见的“不设防”状态。
该发言人指出,近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港独”组织和激进分离势力在外国和“台独”势力支持下,公然叫嚣“香港独立”等口号,煽动无底线的“揽炒”,实施触目惊心甚至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乞求并勾连外国和“台独”势力赤裸裸地干预香港事务。这些违法行径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事实表明,国家安全漏洞大开,全社会都会付出惨痛代价。
该发言人指出,香港自回归之日起就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香港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负有最大责任。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部分立法权,并不改变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也并不因此丧失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有的责任和权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局势且无法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立法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作出有关决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相关法律,是必然选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该发言人指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一国”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也无从谈起。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依法治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决策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的当务之急,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是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该发言人强调,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有关法律,针对的只是那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不仅不会影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而且会使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利益将继续依法得到保护。在国家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香港必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该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如磐石。历史终将证明,伴随着“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国两制”这艘航船必将沿着正确的航向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全球首例水貂致人感染新冠:来自荷兰养殖场,水貂无症状
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事件及相关研究并不罕见,然而来自荷兰的一项调查首次提出:该国一家水貂养殖场里的水貂将病毒传染给了一名工作人员。这与该国此前认定的传播链条相反,也是全球首例水貂致人感染新冠。
根据荷兰政府网站于当地时间5月19日发布的一则声明,“正在对水貂养殖场进行的COVID-19调查的新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可以从水貂传播给人类。调查还显示,水貂感染新冠病毒后表现为无症状感染。”根据这一新的调查信息,荷兰农业部和卫生部正在采取新的措施。
荷兰水貂养殖场暴发疫情最早于今年4月报告。当时在两个养殖场观察到水貂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迹象。截至4月底,一个农场超过2%的水貂死亡,而另一个农场也超过1%的水貂死亡。据悉,荷兰有130多个农场养殖水貂,这种半水栖食肉哺乳动物的价值主要为柔软的皮毛。
根据荷兰政府此次发布的声明,研究人员通过比较病毒在不同动物和人身上的序列,可以创建病毒“家谱”,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人和动物在何时何地被感染。他们在这次水貂感染疫情中通过这种方法发现,水貂养殖场的一名工作人员身上的病毒与该养殖场的水貂身上发现的病毒相似。
基于这种比较和病毒在“家谱”中的位置,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受感染养殖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很可能已经被水貂感染。
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他们认为病毒在水貂养殖场外从水貂传播到人类的风险仍然可以忽略不计。RIVM之前做过风险评估,在养殖场外收集的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病毒的痕迹。
基于这些新信息,荷兰推出了新的措施,所有养殖场的水貂都将接受抗体筛查,该检测将是强制性的,将由荷兰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管理局(NVWA)协调。这种抗体检测可能将强制扩大到整个荷兰境内的水貂养殖场。
声明中提到,如果在水貂养殖场发现病例,将采取与其他受感染养殖场相同的措施,并建议工作人员在工作时使用个人防护设备。受感染农场的动物和粪便被禁止离开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对水貂疫情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在其中一个受感染的水貂养殖场,11只猫中有3只身上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因此,研究猫在传播病毒方面的潜在作用至关重要。在进一步研究之前,建议水貂养殖场的主人确保猫不能进入或离开。
RIVM目前关于COVID-19和动物的建议尚没有改变:如果家里有人出现类似COVID-19症状,并且动物可能已经感染,请将宠物留在室内。
根据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病毒在貂舍外从貂传播到人类的风险仍然可以忽略不计。RIVM之前做过这样的风险评估,因为在貂舍外收集的空气和灰尘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病毒的痕迹。
实际上,除此次水貂感染人类事件外,此前科学家已广泛关注常见动物及宠物在这次疫情中的感染事件。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动物医学院教授、农业部兽用诊断制剂创制重点实验室主任金梅林院士,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高致病性病原生物学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研究员等人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武汉地区新冠疫情暴发后采集的102只猫的血清ELISA检测显示,来自15只猫(14.7%)的血清对新冠病毒的受体结合域(RBD)呈阳性。在阳性样品中,有11份具有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其中主人为新冠患者的3只猫的中和滴度最高,表明高中和滴度可能是由于猫与新冠患者之间的紧密接触所致。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等团队的一项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也指出,来自香港确诊COVID-19病例家庭的15只宠物狗中,有2只狗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只为17岁绝育的雄性博美犬,另一只为2.5岁的雄性德国牧羊犬,另外提及香港也有一只宠物猫感染了新冠。
除这些研究之外,美国的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还报告了5只老虎、3只狮子的新冠感染。此外,美国还报告了1只宠物狗被感染。
2、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直达基层,专家称赤字货币化不会实施
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交大会审议。此前备受关注的抗疫特别国债的相关细节也随报告披露:今年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用于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等。
抗疫特别国债用在哪?
作为对冲疫情影响的三个财政工具之一,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备受关注。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发行特别国债”,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其进一步明确为“抗疫特别国债”,业内认为,这说明特别国债将主要投向抗疫领域。
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使用范围,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节,使用范围被明确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
预算报告中,除提出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外,还增加了“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地方解决基层特殊困难”的表述。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这是基于疫情对各地造成的影响不同而作出的全盘考虑,比如,在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预留部分资金是一种准备,抗疫特别国债的“抗疫属性”没有改变。
何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提高赤字率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要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何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连平解释,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中央的转移支付都是首先给省政府,由省政府具体安排,现在提出“直达基层”,就是直接开出单子,明确每笔钱直接给到哪个基层城市,不再从省政府“过手”,保证这个钱是真正、全部、不打折扣地用到实际所需要的地方去。
“这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上一级财政会截留下一级政府的财政资金,调整到其他项目用途上”,连平认为,报告中“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也强调了这一点。
预算报告明确了特别国债的期限、预算管理及还本付息等事项:抗疫特别国债是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的特殊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还本付息方面,预算报告指出,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
解读:“发债规模为之后的财政政策留下空间”
连平介绍,过去一直都是谁发债谁偿还,这次提出中央财政承担30%,偿还3000亿元,很明显就是用中央财政的能力支持地方财政,相当于补贴地方。
他认为,相比地方,中央财政状况相对比较好,杠杆水平比较低,在国际上横向比较也是较好状态,但地方财政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比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占GDP的比重达到约60%左右,中央财政只占不到30%。
他建议,目前情况下,中央财政可以更多发挥作用,更多举债,地方财政虽然举债,但可以部分由中央来偿还。目前看,也是这样做的。
两会前夕,有学者建议由央行来直接购买特别国债,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讨论。连平表示,从今天的报告来看并没有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赤字货币化仍然只停留在学术领域的探讨,在所能看见的未来,也不会实施,“有些过头。”
针对1万亿元的发债规模,连平认为并不是市场预期的上限。分析原因,他认为,制定规模的时候要考虑财政在其他方面挖掘资源的情况,这次报告也特别谈到要把相对闲置的资金更好地使用起来,同时削减中央财政开支。
“也就是说,如果还有挖掘空间的话,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借太多的债,这样的发债规模也为以后的积极财政政策留下了空间,因为现在都不知道国际市场还会发生什么。”连平分析。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